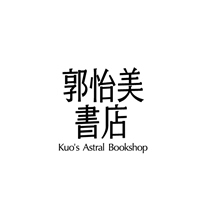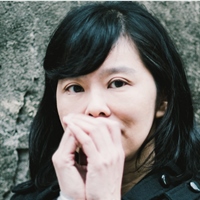當我們談及不限媒介與形式,跟創作並行的特殊存在,必然是評論。
文學、劇場、電影、當代或古典藝術(平面,跨媒材或表演,肢體行為甚至可延伸到體育競賽)、音樂、小至菜餚服飾大至民族文化,有文本與符號聚合處,當作品放置於開放場域,必然遭逢的,是眾多紛雜的主觀意見與愛憎喜惡。
然而評論本身,用一種後殖民式的「誤讀」與「誤用」的觀點探查,至今仍包圍在班雅明談前機械複製時代藝術品時使用的「靈光」一詞。藝術品存有的「此時此地」不可轉移神聖性,被我們轉喻,誤用,擴寫成形塑評論此文類「神秘主義的,難以表述,破譯的,帶距離感且不可侵犯性」。
評論的奇特,更在此類別在不同領域的各自命運。有作家高聲疾呼「台灣書評已死」;但反觀樂評,影評的蓬勃發展,具高親民性(眾人社群無不多少追蹤,關注臉書影評帳號,音樂評論網等等)。創作者兼評論是球員兼裁判?評論該是獨立存有,不受產業脈絡綑綁?評論是絕對的學院派,高度玩弄知識份子的專業詞彙展演?不同創作類別的回答,不同意見,交織出評論這一文類千花百樣的迷人景色。